Henk Vording: 数字时代,税法如何回应?
时间:2020-10-23 来源:对外事务办公室作者: 仇尚卿
2020年10月12日至10月16日,太阳诚集团53138(中国)有限公司全球教席、荷兰莱顿大学太阳诚集团53138教授Henk Vording以“数字时代的税法前沿问题”为主题举办了四场线上学术讲座。张智勇教授主持讲座,校内外两百余名师生参与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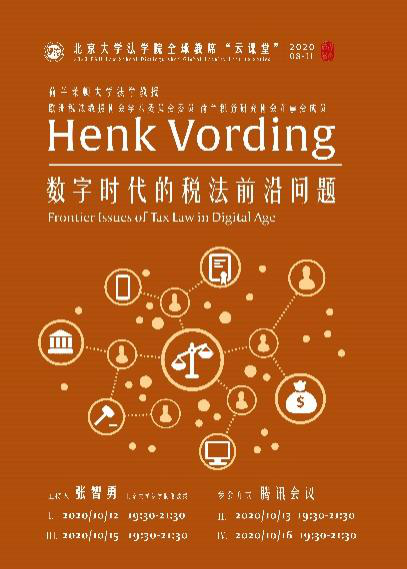
Henk Vording于2006年至今任莱顿大学太阳诚集团53138教授。他曾任美国加州大学黑斯廷斯太阳诚集团53138客座教授。同时,他还是欧洲税法教授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荷兰税务研究协会董事会成员,和荷兰税务改革委员会前委员。他拥有莱顿大学历史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1986 年任莱顿大学太阳诚集团53138经助理教授,2004 年任莱顿大学太阳诚集团53138税法与经济学副教授。他开设的课程包括税法导论,税收哲学理论,欧洲税收政策。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欧洲与国际税法与政策(重点为公司所得税)、税法及其制度的历史发展、税收和再分配的哲学基础。他新近的学术成果包括《荷兰何以成为跨国企业的避税天堂》(2019),《2020年荷兰税收政策说明》(2019)等。
本文以文字实录的方式呈现讲座核心要点。

一、 避税概念认定的疑难问题
Henk Vording:大型跨国公司常通过各种手段避税,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此遭受了惨重的税收损失。一般认为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应缴纳“合理份额”的税款,然而“合理份额”却难以界定。单看一个企业的纳税是否合规显然不够,因为大量善于运用“避税”手段的企业精通各地法律,“避税”过程并不会出现违法行为。对此,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G-20/OECD)也在不断商讨对策,并启动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BEPS)。
对“避税”行为进行规制的初衷并非消灭所有的“避税”行为,许多国家基于跨国税收筹划的可行性,专门出台了优惠的税收政策来吸引投资。此外,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税法的复杂性、专门的税务规划机构,都使得“避税”成为可能。只是,有一些过度避税行为,无论如何都无法满足“合理份额”的标准。
我们可以从“社会契约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社会契约理论提示我们在订立契约之时就应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搭便车”现象,从而在契约中增加各种限制条款。我们在制定税法时也应严格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灰色地带,并考虑其是否符合基本的法理精神。如此,我们才能从源头上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税法。具体而言,税法可以参照社会契约理论,规定跨国公司“进入”某国需遵守的条件;为解决全球范围内征税的困境,社会契约的效力范围也可以相应扩大到区域乃至国际层面,以综合判定企业缴纳的税款份额是否合理。
提问:“社会契约理论”是否使得问题复杂化?
Henk Vording:这里社会契约理论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合理份额”标准的局限性。目前各国税法不尽统一,国家之间条约冗杂,给纳税者的操作空间过大,而逐案分析纳税主体的主观要件又是不现实的,因此亟需更严格的客观规制。社会契约理论为我们指明了,唯有在明确的客观规则确立后,国际社会方能达成一致、共同行动。
二、 经合组织关于数字经济税收的第一支柱方案
Henk Vording:2019 年经合组织通过关于数字经济税收的第一支柱方案(OECD Pillar 1 proposals)和第二支柱方案(OECD Pillar 2 proposals)。其中,第一支柱方案旨在重新进行征税权分配,第二支柱方案则旨在划定最低有效税率,以处理跨境征税问题。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许多大型科技公司(如谷歌、亚马逊、脸书等)都得以通过各种手段不合理避税。一方面,数字化使得大型跨国公司的盈利模式产生了巨大变化,用户带来流量与广告,商标本身带来极为可观的版税。另一方面,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在许多国家或地区不再设立线下实体。二者都加剧了征税的困难。
一般来说,如果要在一个公司的非住所地对其进行征税,则需满足该公司在当地的运营达到成立“常设机构”(permanent establishment)的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在处理数字经济相关的税务问题时心有余而力不足。
经合组织2015年的报告提出了“显著经济存在”(significant economic presence)的概念,即数字化经济使得企业能深度参与一国的经济生活而无需有形存在,从而使得现行的征税联结度规则和利润分配规则不再有效。在2018年的报告中,经合组织分析了数字化对税收的几大挑战,包括有规模而无实体(scale without mass)、公司的无形资产价值、以及高度依赖用户参与的商业模式。2019年公开咨询文件中,经合组织列举了三种征税权划分的方案,以便将更多的征税权分配给与数字化交易活动所创造的价值紧密相关的市场或用户所在国。这三种方案分别为用户参与税收模式(user participation)、营销型无形资产税收模式(marketing intangibles)、以及显著经济存在税收模式。
在2019年形成的第一支柱方案中,经合组织总体采纳了用户参与税收模式,即先从企业全部利润中减去根据独立交易原则分配给企业常规活动的利润,计算出非常规或剩余利润,再依据相关的定量或定性信息确定或者简单地按照一个事先商定的百分比,将这些剩余利润的一部分归属于用户的价值创造活动,最后根据商定的分配指标(例如业务收入)在企业拥有用户群的各用户所在国之间分配相关利润。
提问:经合组织的双支柱方案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否公平?
Henk Vording:经合组织一直希望听到更多国家的声音。不过,经合组织的支柱方案技术性太强,很多发展中国家既没有能力、也缺乏人手真正参与实质性的谈判。此外,许多大型科技公司的用户群也集中在发达国家。综上,支柱方案一的磋商过程恐怕实为发达国家之间的较量。相较之下,支柱方案二会有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三、 经合组织关于数字经济税收的第二支柱方案
Henk Vording:跨国公司有时会将相关利润转移至低税甚至无税实体,引发税基侵蚀的风险。第二支柱提案希望通过国家间联手的方式,化解这一风险。2013年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诞生之初,参与协作征税的国家数量非常有限。
世界范围内复杂的税法体系、避税天堂的存在、征税联结度的要求、滥用税收协定等因素也都为税基侵蚀提供了可乘之机。对此,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确定了三类解决途径,包括制定新规、统一规则、接受监管。
第二支柱方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所得计入”规则(income inclusion rules)和“征税过少的支付”规则(undertaxed payment rule)。“所得计入”规则适用于企业的境外分支机构或受控外国公司。根据该规则,如果企业的境外分支机构或受控外国实体所得在其设立地或居住地适用的有效税率过低,则它们的相关所得应当在企业或股东的居住国征税。“征税过少的支付”规则规定,付款人向关联方支付的某些特定付款项目不得在税前扣除,除非这些支付已按最低实际税率纳税。概言之,对于一个不涉及第三方的跨境交易,住所国(residence state)和来源国(source/market state)都可以对其进行征税,二者形成“互补”。
通过上述手段,第二支柱方案可以实现最低有效税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避税带来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
提问:在双支柱方案下,属地税收主权是否仍然成立?
Henk Vording:经合组织认为,国家当然有权决定其税收制度(比如自行决定是否对利润征税),但其税收主权需要建立在经合组织所确定的基本框架之下。例如,最低有效税率所规定的税率底线是不可突破的。

四、 金融业的税收问题
Henk Vording:对于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来说,通常存在两种政府调控的手段,一是税收(tax),二是规制(regulation)。
税收与规制存在显著差异。税收带来财政收入,但是规制无法做到这点。税收通常是较为宽泛的手段,而规制则针对特定的行为或风险。就结果而言,税收可能会影响社会宏观经济(或至少是所有金融服务的使用者),而规制一般仅针对某部分雇员或投资者作出。无论是税收还是规制,都会增加银行及其客户的成本。不过,税收政策能够确保银行在金融危机时获得政府的财政扶持,而规制的隐含之意则是银行在未来运营过程中很可能需要自担风险。在现实生活中,税收与规制通常并驾齐驱、双管齐下,从杠杆率3%的限制到针对特定金融交易的征税,种类可谓十分丰富。总体来说,税收手段相比规制手段,调控的精细程度要更弱一些。





